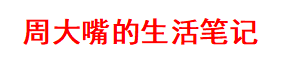那些催人成长的雪
视觉中国供图
编者的话
一场雪后,阳光透过从树上散落的细细的雪粉,闪耀着柔和的银光。青年心中的“雪”,常常饱含着“闪闪发光”的故事。在他们的笔下,雪是景色,也是催动自己成长的动力。
——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编辑部
雪人(小说)
刘琴(23岁,苗族)
母亲急急地走在前面,带动了一阵风。
她频频回过头,吵嚷着说去奶奶家的公交车快赶不上了。我却仍是慢慢地走,犹豫,或者迟疑。已是3月,眼前却忽然飘过一丝雪。我望着那丝雪,落到了很久很久以前。
在你的门前,我堆起一个雪人
南方的冬天是少雪的。而重庆的山却使我们踮起脚,可以触摸到冬天。雪是一点一点落下来的,似作闲庭信步,在地上铺就薄薄的一层。缓缓地,一夜一夜的漫长之后,竟然也全白了。白色的枝杈,银灰的空色。
小小的我不顾奶奶的呼喊,逮到一个机会就跑到木屋外面,用脚丈量冬天。
抬起头,望着门前的青石上,也积了轻而柔的雪,像极了高贵的鹅绒枕头,静静地躺在那里,上面枕着冬天。
二婶家一片喧哗,原来是她在院前堆了一个大大的雪人,正用铲子狠狠地拍打结实。小哥哥快乐而着急地跑来跑去,鼻子也像极了雪人脸上的胡萝卜,红红的。
需要一个小雪人代我守候
我忽然想起那枕青石,需要一个小雪人代我守候,以免沉睡的冬天在半夜醒来,哇哇地叫着奶奶。而我的奶奶此刻一定沉睡着,打着呼噜。她只听得见自己孙女特有的声音。
我放开随手抓的两把雪,小心翼翼地把头伸向屋檐。上面的瓦一片一片,我却只用手捧最干净的雪。很快雪人便做好了,下身是双拳大的圆,上身是只有橘子那么大的雪。
橘子?我低着头,仔细凝视着或洁白或透明的雪球,心里生出无限的怜爱。家里没有胡萝卜,我正犹豫着用什么来给它添上笑脸。一下子,像有一股泉水流过全身——橘子皮便是她最好的笑脸。
你拿出一颗糖,一颗甜甜的心
木屋里面又是另一种时光了。银色仅在门口的木板上坐着,屋子里是一片黄澄澄的光,暖暖的,像秋天又像春天。我小心翼翼地跑进去,木门后面有我想要的橘子。我高兴地回过头,而奶奶却站在身后了。
她并不恼我,只是微笑着说不能吃太多,不可以外出玩耍,然后把我连人带橘子一起拎进了火柜里。打开方脑壳儿的电视,又捧出许多只有过年才吃的糖果,她却总是忙着,让我好奇大人哪里有那么多事情呢?
室内越温暖,室外便越暗。奶奶终于和我一起坐在火柜里,手里却还是不肯停下,好像在打粉色的毛线鞋吧,嘴里继续着不要出去、太冷的碎碎念。
于是我和她说起我的雪人,我和她讲我看见的冬天:冬天很美,纯洁得想叫人抱一抱。但却又怕把她弄醒,于是堆了雪人守夜,可它还需要橘子一样的笑脸。
奶奶又好笑又吃惊地看着我,停下了手里为我做的毛线活,答应明天中午可以出去一小会儿。而这时候门响了,是二婶进来了。一脸的寒冷和水汽,映着灯光,或许是雪化的水珠吧。
我并不在意熟人的到来,高兴地一会儿吃糖,一会儿看电视,一会儿钻进火柜里。紫红色的毯子盖在头上,里面黑黑的,而炭火们却抱在一起,发着讲不出颜色的光,很温暖,就和口袋里未融化的糖果一样。隐约听见她们提到了我的名字,似乎有什么不一样。我盯着炭火,选择专心听自己怦怦的心跳。
雪人没有笑,一直没有作声
不记得那天怎么睡的了,仿佛火在一点一点变暗,最后变成了雪人的笑脸。而大人们还在讲着,声音一点一点变小了。
我醒来时安然地躺在木床上,身边空空的,奶奶已经起来了。火柜里又是一盆旺旺的火,我剥着橘子,一个,两个,然后把橘子皮放在从灶头拾来的透明塑料口袋里,等待着雪光再到屋前坐。
等待的日子仿佛特别特别长,真的就想这样跑出去啊!但我还是乖乖地等着,坐着。
早饭之后我终于鼓起勇气问正在洗碗的奶奶,我可以出去了吗?“可以呀。”我本能地想听到这样的回答。而耳朵反馈说,“是明天呀!”
于是明天又明天,橘子皮一点一点变得干瘪,在火柜里放着,散出阵阵的香。奶奶说,雪人也在一天一天长大,等春天到了,它们就会遇见最美的颜色,变成更好的自己。
原来明天以春天为期,我温驯地点点头,认真地数着奶奶或自己剥的橘子皮,期待着春天的相遇,许诺着无数次再见。
直到母亲的忽然到来,说开学的日子近了。太阳很好,该回家了。
哦,春天到了吗?我跑出木屋看见一个很大很大的太阳。山又变成黛色,屋檐下的水一滴一滴地落,门前的大石青青的,只有些水光在闪烁。
“奶奶,雪人呢?”我直视着太阳,想哭又迷惑,想着再也不要回来了。
直到春天的骄阳,把它融化干净
木屋又在眼前,我到底还是回来了。它沧桑了许多,黑瓦泛出微微的白,院前的两侧则是满眼的青苔,叫人担心会不会摔倒。
母亲走在前面,而我踌躇着,不愿进去。别过头,看见二婶在自家的院子里择菜,于是那个红鼻子男孩儿又跃然心头了。“哥哥怎么样了?”我微笑着。她一怔,抬着头露出复杂的凝色,极光亮却又极暗淡。
母亲尴尬地打了招呼,快速地拉我走了。她对我说:堆雪人的男娃走失了,那年下了好大的雪,二婶连夜发了疯似的找,却连鞋印子也没找着,不是还上了咱家去吗?
我定在那里,忽然明白二婶那年脸上的,不是雪。我忽然懂得,我欠奶奶很多很多次再见,于是开始跑,想要跑过时间,想要回到很久很久以前。
人在哪里呢,心在哪里呢
奶奶病重躺在床上。我慢慢地走近,竟忽然觉得不认识了。没有丰满的慈祥和记忆的轮廓,骨瘦如柴的老人挣扎着起来,原来小小的木床添上一床又一床的被子,却仿佛大了许多。
“妹,你归屋了,我在等你嘞。还能走的时候,我就经常带把小板凳坐在屋檐下,看天上的云,云就变成你们的样子,和我讲话。后来走不动了,我就躺在床上想云,想你们都在做哪样。”
“村里头的老人家一个个都走了,这回,怕是要轮到我了。山里头春天的时候会长出好多草,风一吹,就成为天上的云啦。”
“担心你和你父母,他们爱热闹,你爱吃拿橘子皮熏的腊肉。等他们老的时候你一定要经常回去看哈。对他们好点,他们当初养你不容易,受不了这份冷清,也是看不懂天上的云。我还悄悄地给你留了点腊肉放在柜子头,是拿橘子皮熏的,莫给别个晓得。”
“妹莫哭啊,以后想我的时候你就看天上的云,我也看你们……”
小小的泪潭边,只有蜜蜂
我点着头,却早已泪流满面。时光一点点汇聚起来,从幼儿园到中学,从童年到少年,拼成一幅东边日出西边雨的画卷。小学时我如何不知道父母是为我好,只是我一直着眼于那些表面的小事,而忽略了亲人对我的爱。幼年时我如何不知道奶奶的话,只是面临着满天的云,我却死盯着地上的水不放!
只是面临着温暖的太阳,我却坚守着心中的寒冷。只是因为我不能理解,所以坚信那是谎言。只是站在晴与雨的中间,我背对太阳,选择了雨的一面!
离开的路上,我看见那丝雪落到了一方矮矮的坟墓边。青了苦草,于是蜜蜂在白花处环绕。太阳大大的,一朵流云闲定,像极了小小的雪人,凝视着那年的遇见。
我跑上前,挽了挽母亲的手。忽然发现母亲其实走得很慢,慢得像天上的云。别过头,我想要给她一个大大的笑脸,却看见风又吹白了几缕青丝,飘起一丝雪。
雪晴云淡日光寒(随笔)
邹贤中(33岁)
我出生的湘南农村四面环绕着青山,无论房屋何种朝向,都能开门见山。湘南的雪并不是入冬就下,而是集中在腊月和翌年的正月里,断断续续地下三四场雪后,才进入春天。一下雪,开门见雪的景观就这样映入眼帘。
下雪前是有征兆的。为了防寒,农村人家的窗户会蒙上一层厚实的薄膜。下雪前的夜晚,不稳定的气流作用在窗棂薄膜上,会刮得薄膜噗噗作响。冬日的夜晚,裹着被子睡在铺着厚如棉絮的稻草木架床上,闻着稻草散发的绵长清香,那是一件极其幸福的事。在即将进入梦乡的时候,隐约间会听见一阵淅沥淅沥的清脆声在瓦面上响起,恍如调皮的孩子在高处往瓦面上扔下了一把豆子,那细碎的声音清脆悠长,在寂寥的冬夜有鸟鸣山更幽的味道。这时,母亲会在暗夜里睁大了眼睛,凝神倾听一会儿,然后欣喜地对我们说:“下雪了!”
其实,母亲所说的下雪,还不是真正的雪,而是一种叫“霰”的固态小冰粒。霰洒向瓦面的声音越来越小,渐渐消失了。无声无息的雪花然后才缓缓降落,陪着我们进入梦乡。
第二天一早,平时穿衣起床磨磨唧唧的我们,如不怕冷的小兽般蹿出了家门。“吱——呀——”随着门扉打开,展现在面前的是一片银装素裹的世界。雪打在人的脸上冰凉入骨,在体温的作用下很快就化为了水。落在人的头上、肩上,就积存了起来,如果人长时间站着不动,就会与大地连为一体,成为白茫茫的一片了。极目四望,那雪落在山尖上、树梢上、瓦面上、大地上……到处是无瑕的雪。雪如一个参透世事、大彻大悟的高人,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将美好、善良、肮脏、罪恶一并接纳、覆盖。
禾坪上,铺着一层厚达一寸的雪,那是一片尚未被涉足的世界。我和哥哥如撒欢儿的小马驹在上面疯跑,所到之处,在雪地上印下一行行凌乱的脚印。母亲的呼唤从里屋传来:“还不快点回来吃饭,上学都要迟到了。”
我和哥哥一溜烟跑回屋里,火塘里燃起了熊熊大火,奔放的火焰在火塘上空摇曳着,屋里温暖如春。我们鞋面上细碎的积雪在炙烤之下瞬间融化,化为蒸汽冉冉上升,在屋里飘忽着出了窗户,最终消失在茫茫旷野中。
吃过早饭,该去上学了,这才发现那条平时绿荫遮天蔽日的山野小径此时被积雪覆盖,再被夜里的朔风一刮,已经冻上了一层坚硬的冰层。父亲用一把锄头将下山的路,以60厘米的间距整齐地挖出了一条父爱的“天梯”,才算是解决了下山难的问题。
去上学的路上,到处是白茫茫的雪,田里有泛青的白菜尚未被积雪完全覆盖,露出青葱色的叶子,与大雪顽强地作斗争。路旁的树枝上,下滴的雪水凝固成冰柱,悬挂着,长短不一,如倒悬的钟乳石。路上遇到三三两两的同学,大家追逐打闹,到了学校,人人身上带雪,无一幸免。就是在课间休息时间和放学路上,也少不了打雪仗。
家庭富足的孩子,在玩雪上更有了创新之举,他们买来鞭炮埋入雪团之中,只留下一根引线在外。点燃鞭炮,将雪团抛向空中,待鞭炮爆炸,只见雪团四面开花,好像下了一场急切的雪雨。
我曾独自一人在凌晨的雪夜里行走。
那时,哥哥已远去深圳打工。傍晚时分,天上下起了鹅毛大雪。下到了半夜时分,整个村庄银铺世界,玉辗乾坤。那洁白的雪成了一面巨大的反光镜,将大地映衬得如白昼一般,也难怪晋朝的孙康能够映雪读书了。这状如白昼的雪夜扰乱了母亲的生物钟,她以为天已放亮,在这种潜意识的影响下,母亲看错了时间。我吃过母亲做的早餐,背上书包独自走出家门。
大雪茫茫,均匀地铺盖在大地上的每一个角落。路上的雪完美无瑕,连一个脚印都没有,更别提见到人影了。想到自己竟是今天最早出门的人,内心欢欣雀跃地躁动着,似乎有一团火在心头燃烧,抵御了无边的寒意。走到村里的代销店时,想起一位要好的同学,我决定邀他同行。敲门半晌,屋里才传来他母亲惊讶的声音:“你怎么这么早,现在可是凌晨两点。”
我吓得一个激灵,说:“不可能吧?我都吃了早餐要上学了。”
屋内,灯亮了。她的声音传出来:“现在真的是两点。你妈妈看错时间了吧?要不在我这里挤一下再睡会儿吧。”
想到在别人家睡觉多有不便,我决定赶回去睡一个回笼觉,便跟她告辞了。走出数步,她屋里刚扯亮的灯又灭了。之前的欢欣雀跃已经变成对深夜的恐惧害怕。回到家,母亲知道自己看错了时间,后怕不已。
那是我唯一的一次雪夜之行。
让人成长的不是岁月,而是经历。那一刻的经历,让我瞬间长大了。就这样,突然之间,我敢走夜路了。
那一日的雪路,让我和父亲变得更亲密了些(随笔)
陈龙(28岁)
那年冬天,我和父亲邂逅了一场久违了的雪,在心中留下了属于雪的永久记忆。
人们一开始是幸福地打开大门迎接雪的,可它的到来却是没有节制的奔放——一个月都没有停下,仿佛要一次释放掉它所有的能量。到最后,它留给人们的痛苦就比幸福多了一点,那一年的麦子差不多都被它“带”走了。
我家坐落在群山怀抱的山谷中,从家到学校要越过几座山峰,若赶上雪天,父亲便和我同行。玲珑剔透的水晶球世界,应该是白雪公主降临人间的时刻,但这一切只会发生在童话里。大雪把整座山都覆盖了,并且经过几日的积雪、低温,路面上都结了冰溜子,仿佛成了一个滑雪场,走在上面,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,仿佛都回到了初学走路时的模样。不过,若是喜欢滑雪、溜冰,此刻正是一个绝妙的机会,到处都是展示你才华的场所。但我不行,虽然我喜欢体育运动,可在滑雪方面,我完全是个外行。
在动身出发前,我和父亲就在鞋底打下了草结,并备好了树枝做的拐杖。走在山腰时,他走在前面,我紧跟其后,但他还是不放心,仍时常回头叮嘱我说:“打横着走。”我们都尽量让自己的身体降低,尝试与雪地保持平行,让手在脚的前方领路,活脱脱像两个小老头。那一场大雪让我和父亲的年龄和经历差距减小,变得更亲密了些。狼狈的我们,一前一后不停地在路面上重复着跌倒和爬起的动作。
在一次次的跌倒中,我的手脚早已失去知觉,变得麻木,衣服上的积雪也没有力气清理,任它融化,与体温融合。额头的汗水时常进到眼里,和无辜的泪水相遇。父亲始终在前方,拉着我的手,那年,他已40岁,近距离地看着他在雪地里摔跤、打滚,他的身子骨肯定也不好受。
时至今日,我仍忘不了那一日的雪路,没有什么能比它更亲切的了。并且,我开始有点怀恋那时不停跌倒和爬起的感觉,我不会忘记全身僵硬时,泪水与汗水的交融;我不会忘记我的父亲,始终在前方领路。
纯白何曾堕尘埃(小说)
刘臻鹏(23岁)
北方山村里的野狗吠了几声,连绵的山谷与高低不平的地势将这声音的音量和层次感调大,回音在触碰到家家户户人耳的时候才会消散。远远望去,黑夜之中,天上白银色点点,地上隐约的一些暖荧色点缀山脚间。
小追在房间里看着小人书,旁边的油灯影影绰绰,发出噼里啪啦的微小声音。阿婆早已躺在了床上,裹了两层棉被。疲倦时,小追推开房门,发觉院子里不知道何时起下起了鹅毛大雪。这些天之精灵将下坠的过程演绎成一个慢性的垂线运动,并不纷扰胡乱飞舞。它们遵循着各自的轨迹。
小追抬头,看着一个个纯白的小点好似在逐渐放大、圆润,接近他稚嫩的睫毛时,已是一层湿润脸部的轻纱。触碰到眼角周围的那个瞬间,他感到一阵酥麻,雪便融化得无影无踪,一半成了水,在他脸庞浸润,另一半似乎进了无形的气,让周围空气变寒,自己的躯体却更感到暖和甚至炽热。
“孙儿,快回屋里吧,外面冷,别受了风寒。”沉醉其中的小追突然听见了阿婆的呼唤,此时阿婆已下了床,倚在了木门旁。因为下雪算是件稀奇事,所以他是不情愿回屋子里的,但是他怕阿婆受风寒或者为他担忧,便回了屋子。关好木门的瞬间,他耳朵里忽然清静了,清静得有些荒芜。
时光流逝,大山绿了又青,青了又绿,永远无言,变的是山里的孩子们,即将扑扇着自己的翅膀飞出大山了。小追想离这个小山村远远的。他从这里出生,但他想脱离这个小地方,在大城市里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。他打算前往三亚生活。临走前,正是雪夜。当天夜里有风。他逆着风往前走,他走出这段崎岖的山路才能在车站坐上车,开始旅程的第一步。
这一次,雪很小,却纷飞得晃他的眼睛。他心里笃定着南方,却被风雪吹打得生疼,走这段泥泞山路的时候,他心里什么也没有想,理性且面无表情,像是平静的海面。直到山路走到尽头,他即将正式跨出这个村子的时候,他才下意识地回头望去。曾经就是他的全世界的山村,如今在他视野里竟如此渺小,各种雪白的残缺的斜线和密集的颗粒笼罩着这个山村,也呼应出了他扎在心底的料峭冰川:对阿婆的不舍。
坐上火车之后,小追终于捂着脸,无声地抽泣起来。火车逐渐接近南方,却拉远着他与阿婆的距离,也越来越用力地撕扯着他随着变远的距离而即将破碎的心。此刻,他之前积蓄着的、对外婆总是啰唆而产生的不耐烦,早已被舍离的滔滔苦水冲散。原来,他走山路的时候刻意什么都不想,是怕自己一旦想到即将与阿婆分隔两地,不舍的感情就会冲破自己虚设的理性心理防线,让他在这感情的水流中重新返回阿婆家。
在南方摸爬滚打的日子里,小追几乎没见过下雪。这里常年高温,他一开始也是从事一些体力活。夜晚,他经常登上免费的景观楼高处,看着黑暗中地上各种强度的灯光,好似家乡溪流里的粼粼水光,只不过这里的“水流”是纯黑或黛紫色,鸣笛声和鼎沸的人声令他耳朵被填满,心里却荒芜无物。但是既然已经选择了来到大城市打拼,那么他是必然不会走回头路的。
在漂泊沉浮了几年后,小追手里已经有些积蓄。他在节假日前往一个艺术家画展进行参观,眼前各式各样的画令他感到费解又无感。直到眼前出现一幅画,缠住了他的脚步。画中,山脚下有一个屋子,在雪中明明暗暗着。
他的心被重重地敲了敲。幼时,他只想逃脱故乡的束缚,即便童话世界般的雪花也无法吸引他留恋。如今,他拿着用省吃俭用的工资买的入场券,在画展中用干涩的眼球定格着一幅艺术画,在一个被框在方格子里的扁平的纸上回忆着那些雪、那些人和那些事。
年底,小追飞回了北方,回家。下了飞机,他感到了阵阵的刺骨的寒冷,自我打趣道:这就是故乡给我的欢迎仪式吧。他加快步伐,朝着阿婆的家奔去,心窝子逐渐暖起来。天公不作美,故乡没有碰巧下起雪,没有让他重温心心念念的场景。与阿婆重逢的时候,他的嘴张了又闭,有好多好多话要讲,但又一时不知从何说起。眼神重归温和,一切尽在不言之中。
灶房中,阿婆不再和从前一样一个人做菜,多了一个长大成人了的小追。他走进原本他睡的那个小房间,角落里那些小人书已字迹难辨,但一向节俭的阿婆却并未将其当作废纸卖掉。夜深了,阿婆想去点亮悬挂在书桌上的那盏油灯,却因腰逐渐佝偻而不再能够到那盏油灯,小追此时已能轻易够到那灯,将里面的芯子点燃。阿婆又习惯性地唠叨道:“晚上尽量少看会儿书,伤眼。”
油灯被点亮的那个瞬间,屋内又燃起暖橘色的光,小人书将他的心理暂时地变回童年,晚餐时饭菜的香气未完全退去,一切又与记忆深处的最初重合在了一起。唯一变了的,是阿婆的提醒不再刺耳,这提醒和每天将其唤醒的第一缕晨光一样舒适。明明暗暗间,窗外透着虫语般微小的声音,是否突然降雪了呢?小追不得而知,也未推门出去验证,他起身,盖紧了阿婆的棉被。
看雪是其次。他不怕自己受凉,他怕阿婆担忧。
来源:中国青年报
免责声明:本文由用户上传,此文本数据来源于原作者,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!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。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,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,我们将及时更正、删除,谢谢。